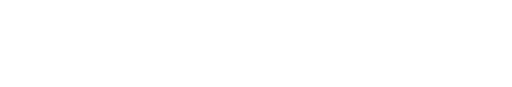推進(jìn)新課程改革�,打造高效課堂學(xué)習(xí)材料之30
編者按:
本學(xué)期在各位參編教師的共同努力下,我校學(xué)案已投入使用���。但我校課堂教學(xué)督導(dǎo)組在聽課的過程中發(fā)現(xiàn):一些學(xué)科、一些教師使用地較好���、部分教師偶爾使用,但也有一些教師完全就沒有使用��;還有的教師把學(xué)案只當(dāng)做課后練習(xí)來使用�����,在使用學(xué)案的教師中�,有的教師不注重預(yù)習(xí)結(jié)果的反饋���,不在預(yù)習(xí)的基礎(chǔ)上講授,仍然是面面俱到���,學(xué)案和教學(xué)兩張皮����。
不使用學(xué)案,不正確使用學(xué)案�����,我們學(xué)校提出的“學(xué)生思維在先”的理念就不能很好的得到落實��,從學(xué)案本身來講�,也就不可能得到完善和豐富。
不使用學(xué)案有很多理由��,如:學(xué)生沒有時間預(yù)習(xí)�����;學(xué)生不會預(yù)習(xí)����,提不出問題���;學(xué)案質(zhì)量差等等。但我們認(rèn)為����,根本原因還在于新的教學(xué)理念還沒有引起大家的足夠重視����,滿堂灌�����,以教師為中心�����、為主體的觀念還在影響著我們的教學(xué)行為�����。
本期推薦的這篇文章�����,就是想讓大家在這方面引起重視�,加強(qiáng)研討���,共同打造高效課堂��。
科研處 2010-12-13
把學(xué)生帶到高速公路的入口處
一���、課堂教學(xué)的隱喻:教學(xué)的核心即學(xué)生主動學(xué)習(xí)和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
對于課堂教學(xué)���,美國哈佛大學(xué)有一個絕妙的隱喻:“到哈佛學(xué)習(xí),就像是很快幫助我找到了高速公路的入口處��。”與這一隱喻相呼應(yīng)的�����,是哈佛大學(xué)名譽(yù)教授程介明先生講的《墻上的洞》的故事��。
故事發(fā)生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條窮人街上��。窮人街的孩子沒有錢��,不能進(jìn)學(xué)校讀書�����,整天在街上游逛��。試驗者為了探明窮人孩子是否有學(xué)習(xí)欲望和學(xué)習(xí)能力��,便在墻上開了一個洞,洞的大小正好能嵌進(jìn)一臺電腦���,洞的高度和孩子的身高差不多�����。孩子只要觸摸�,就可以上網(wǎng)��,但必須用英文��。這一裝置給孩子們帶來極大的新奇感����,大家圍攏在一起議論起來,有的還動起了手�����。一個星期過去了�����,有少數(shù)幾個人觸摸到了門道��。兩個星期過去了����,不少孩子初步學(xué)會了用英文上網(wǎng)�。三個星期過去了,窮人街上的孩子��,你幫我�����,我?guī)湍?��,幾乎都會用英文上網(wǎng)了����。故事后面有三個問題:他們在學(xué)校嗎?回答當(dāng)然是否定的�。他們在接受教育嗎?回答是“不知道”。他們在學(xué)習(xí)嗎?回答:“是的��,他們在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。”
故事簡單�����、淺顯�����、普通�,但含義很深刻���。故事生動地告訴我們:孩子有學(xué)習(xí)的天性��,他們渴望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,關(guān)鍵是激發(fā)和保持他們學(xué)習(xí)的欲望和熱情�;學(xué)習(xí)是自己的一種建構(gòu),建構(gòu)的基礎(chǔ)是已有的經(jīng)驗��,建構(gòu)需要支持性的環(huán)境和條件����,建構(gòu)的特征是發(fā)生變化:有教師在旁邊可能是一種學(xué)習(xí),也可能不是一種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�,教師不在旁邊��,倒可能是一種學(xué)習(xí)�。“墻上的洞”就是要幫助孩子找到高速公路的入口。
其實���,這個故事也是一個隱喻�����。它和“高速公路的入口處”一起����,揭示了教學(xué)的幾個基本要義�。第一,學(xué)生的學(xué)習(xí)就是在路上行走����,但只有在高速公路上才會走得順暢,也才會很快到達(dá)目的地�����;第二,要走上高速公路��,必須先找到入口處��,而找到入口處是學(xué)生在教師幫助下的結(jié)果����;第三,尋找高速公路入口處是一個探究�����、發(fā)現(xiàn)���、辨別方向和選擇的過程�����,需要能力和合適的方式��;第四����,學(xué)習(xí)終究是學(xué)生自己的事,教師的任務(wù)在于和學(xué)生找到入口處�,即幫助學(xué)生打好基礎(chǔ),讓學(xué)生有“帶得走的東西”�����,如此等等���。總之概括起來��,這一隱喻揭示了教學(xué)的核心問題��,即是學(xué)生主動學(xué)習(xí)和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。
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,這一基本判斷都是正確的�。我們應(yīng)該重溫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及其建議。為了使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及會員國制定教育政策時科學(xué)的參考��,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專門成立了國際教育發(fā)展委員會����,在一年內(nèi)研究70多篇有關(guān)世界教育形勢和改革的論文,充分吸收了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5年的思考與活動過程中所積累的經(jīng)驗,于1972年提交了報告���。報告中明確指出:“教學(xué)過程的變化是:學(xué)習(xí)過程現(xiàn)在正趨向于代替教學(xué)過程�。”報告還專門設(shè)立了“學(xué)習(xí)者在學(xué)校生活中的地位”專題��,指出:應(yīng)該使學(xué)習(xí)者成為教育活動的中心��。”對此還進(jìn)一步闡述:“現(xiàn)代教學(xué)�,同傳統(tǒng)的觀念與實踐相反。應(yīng)該使它本身適應(yīng)于學(xué)習(xí)者��,而學(xué)習(xí)者不應(yīng)屈從于預(yù)先規(guī)定的教學(xué)規(guī)則”���,并把它作為一條重要原則:“如果改革不能引起學(xué)習(xí)者積極地親自參加活動���,那么,這種教育充其量只能取得微小的成功�����。”報告鄭重地宣告: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為他自己����,‘變成他自己’。”報告如此不厭其煩、不厭其詳?shù)仃U述�,無非是強(qiáng)調(diào)一個重要的觀點:教學(xué)的核心是學(xué)生主動學(xué)習(xí)、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�。這是教學(xué)改革的方向和原則,是教學(xué)改革的重點和難點����,是衡量和評價當(dāng)下及今后教學(xué)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標(biāo)尺。
改革的方向����、原則���、重點如此明確����,對教學(xué)深刻變革的呼喚如此強(qiáng)烈��,但并沒有引起我們普遍的重視�,教學(xué)還沒有根本性的實質(zhì)性的變革。用“教學(xué)的核心是學(xué)生主動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�、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”這根標(biāo)尺去觀測、衡量和判斷���,我們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��,當(dāng)下的課堂教學(xué)距離這一要求還很遠(yuǎn)很遠(yuǎn)���,“把學(xué)生帶到高速公路的入口處”的意識還未真正確立起來。說得尖銳一點��,有的課堂教學(xué)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盲目地轉(zhuǎn)悠�����,離入口處是如此遙遠(yuǎn)�。因此,教學(xué)改革需要這樣的隱喻��,并亟需將此化為具體的行為�。
其實,在中華民族文化中���,早就對“教”與“學(xué)”的關(guān)系作了非常明確的規(guī)定���。在商代�,甲骨文中已出現(xiàn)了“教”字��,也出現(xiàn)了“學(xué)”字���。通過分析���,可以推斷“教”字是由“學(xué)”字發(fā)展而來的?�!渡袝?middot;說命》里說“學(xué)學(xué)半”�,認(rèn)為“教”與“學(xué)”本是同一個字,“教”與“學(xué)”在本質(zhì)上具有同一性��。戰(zhàn)國時期的《學(xué)記》里還提出了“教學(xué)相長”�����,宋人蔡沈注:“學(xué)�,教也……始之自學(xué)�,學(xué)也;終之����,教人����,亦學(xué)也��。”意思很明確:“教學(xué)相長”的實質(zhì)是“教即學(xué)”�����。教即學(xué)���,教為了學(xué)��,教的核心是學(xué)生的學(xué)����,這就是“教學(xué)”的本義和真義�,是教學(xué)成功的真諦�。遺憾的是,我們常常忘掉這些智慧的古訓(xùn)���。我們?nèi)绻€固守以教代替學(xué)生的學(xué)�,那么可以說,今天的教學(xué)不是在進(jìn)步���,而是在倒退�����。
隱喻��、故事����、古訓(xùn)��,似乎不約而同地印證這么一個深刻的道理:課堂教學(xué)要把學(xué)生帶到高速公路的入口處�。應(yīng)該說,這是教學(xué)的本質(zhì)���,是教學(xué)改革的基本方向�。
二���、智慧:課堂教學(xué)給學(xué)生的“帶得走”的東西
尋找高速公路的入口處�����,繼而在高速公路上自信地快速行走���,需要知識、能力���、方法��,還需要情感���、態(tài)度、價值觀的支撐與伴隨�,否則尋找與行走將是一句空話。但是�,并非所有的知識�����、能力����、方法�����、情感��、態(tài)度����、價值觀都能夠一直伴隨學(xué)生,都能給學(xué)生以信心和力量����,同時,不少知識�����、能力�、方法等只留存在教師那里,甚至只留存在書本里和試卷上�。如此��,學(xué)生尋找高速公路的入口處,必然會顯得“勢單力薄”��、力不從心�����,必然會茫然����、困惑���,只能迂回曲折�,甚至永遠(yuǎn)尋找不到那個入口處�。當(dāng)下課堂教學(xué)最大弊端正是如此:學(xué)生學(xué)的只是符號化的知識,而知識與能力分離;學(xué)生獲得的只是分?jǐn)?shù)�,而分?jǐn)?shù)與能力、與方法����、與真正的情感“絕緣”,用最通俗的話來說:所學(xué)的東西都“還”給了老師��。于是���,給學(xué)生以“帶得走”的東西成了課堂教學(xué)改革的重要命題�。
顯然���,“帶得走”也是一種隱喻���。它生動形象地提醒我們:課堂里學(xué)的東西,應(yīng)該讓學(xué)生帶得走�����,應(yīng)該陪伴學(xué)生行走�����,應(yīng)該不斷“發(fā)酵”給學(xué)生以刺激,提供能量��,促進(jìn)學(xué)生發(fā)展���。可以說�,“帶得走”的東西是學(xué)生可以終身受益的。
從學(xué)理上分析��,“帶得走”的東西應(yīng)具有以下基本特點:①基礎(chǔ)性�����。基礎(chǔ)是不可代替的�,甚至是不可超越的,基礎(chǔ)是穩(wěn)定的����,同時它具有再生性,再生出新的知識���、新的能力���,等等,因而可以持續(xù)地影響人的發(fā)展。②內(nèi)生性��。所學(xué)的知識等有一個內(nèi)化的過程���,與原有的經(jīng)驗相契合���,真正成為“自己的”東西,有的會融入自己的心靈�,積淀為人格,表現(xiàn)為氣質(zhì)���,外化為行為習(xí)慣�。③轉(zhuǎn)化性�。知識遷移促使知識轉(zhuǎn)化。知識可以轉(zhuǎn)化為能力����,使個體得以以個人的方式來理解、洞察�、體會、感悟����、認(rèn)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����。④隱含性���。所學(xué)的知識鑲嵌在自己的經(jīng)驗背景中,隱含著一些思維模式和個人化的觀察視角����,一旦有了合適的條件,就會表現(xiàn)出來���,顯示出特殊的認(rèn)知意義�����。⑤遲效性���。“帶得走”并不意味著立即生效,相反�,往往在經(jīng)歷漫長的過程后才會顯現(xiàn),產(chǎn)生效果�,而這種遲效往往可能真正有效、甚至長效���。
“帶得走”的東西內(nèi)涵雖然相當(dāng)豐富���,但它凝聚在一個概念中����,那就是“智慧”���。智慧是一個綜合體�,是人的綜合素質(zhì)的集中體現(xiàn)�,在內(nèi)涵上,涵蓋了知識���、能力�、道德���、情感��,等等���,它與“帶得走”的東西相契合。其一���,智慧與知識具有同一性���,但超越知識��,是各種知識綜合運用的結(jié)果����,“知識就是力量”�����,而“智慧使人自由”�����。其二�����,智慧以能力為載體�,往往表現(xiàn)為應(yīng)急情景下處置問題的能力�����。但無論是內(nèi)涵還是外延,智慧都超越能力����。其三,智慧與道德同行�����,道德支撐著智慧���,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�����,智慧是對人類有利或有害的事采取行動的能力結(jié)構(gòu)�。缺失了道德���,聰明只能是聰明����,而絕不能稱之為智慧�����。其四,智慧的核心是創(chuàng)造��?���?傊腔凼侨松囊环N高度����。智慧是可能“帶得走”的。在形成的機(jī)理上��,它也與“帶得走”的東西相一致����。比如�����,智慧是知識的活化�����。知識只有在運用中��,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才轉(zhuǎn)化為智慧。因此�����,讓知識“活”在探究中�����,“活”在體驗中�,“活”在實踐中,是“轉(zhuǎn)識成慧”的必要條件����。再比如,智慧往往是對情景的認(rèn)知���、辨別與頓悟�,智慧伴隨著情景��,因而是生成性的�����,是“帶得走的”。
從以上的分析不難得出一個基本判斷����,即智慧是“帶得走”的,“帶得走”的東西總是呈現(xiàn)為智慧���,以智慧來概括“帶得走”的東西�����,是合適的��、準(zhǔn)確的���。如果說,“帶得走”是一種形象化的說法�,是一種形象化的說法,是一種隱喻�����,那么�,智慧則是“帶得走”的總代詞和內(nèi)核����。
學(xué)生正是在智慧的伴隨下����,去尋找高速公路的入口處�����。其實����,尋找高速公路的入口處的過程,也正是智慧生成���、生長的過程����。智慧與“帶得走”的東西這種相互指代的關(guān)系����,及其基本特征和產(chǎn)生的機(jī)理,從另一個側(cè)面啟發(fā)著課堂教學(xué)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學(xué)生主動學(xué)習(xí)��、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。首先����,智慧是不可“告訴”和灌輸?shù)摹墨@取的方式看�����,知識是依靠外在的方式獲取的��,而智慧則是個體內(nèi)心生成的�����。只有當(dāng)學(xué)生心靈敞開的時候����,思維處在積極狀態(tài)的時候,即主動學(xué)習(xí)的時候��,智慧才會活躍起來���,才會冒出綠芽�����。顯而易見��,學(xué)生主動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�、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�,習(xí)得的不僅是知識�����,而且是學(xué)習(xí)的能力�,更重要的是智慧。其次�����,智慧與知識等相比較具有超越的意義��。它超越測驗和考試���,超越功利����,超越工具理性。為測驗而學(xué)���,為考試而教�,絕不會產(chǎn)生智慧����,絕不會讓學(xué)生“帶得走”,即使“帶得走”��,也只是帶走了死記硬背的痛苦和失敗的記憶����。它超越課堂,甚至超越時空����,指向未來。在這一理念的引領(lǐng)下�����,課堂聯(lián)結(jié)的是學(xué)生的未來以至終生�����,聯(lián)結(jié)的是學(xué)生的生活以至整個世界,學(xué)生獲得的是一種持續(xù)起作用的學(xué)力����、再生力���,因而是“帶得走”的����。正因為此���,英國哲學(xué)家懷特海說��,認(rèn)知教育總得傳授知識����,但千萬別忘記�,有一樣?xùn)|西比知識模糊,但更偉大�,在教學(xué)中更居主導(dǎo)地位,人們把它叫作智慧�����;也許你可以輕而易舉獲取知識,但未必輕而易舉獲得智慧�。為智慧的生長而教,應(yīng)當(dāng)居于課堂教學(xué)的主導(dǎo)地位����,讓學(xué)生在主動學(xué)習(xí)、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中獲取智慧����,獲取“帶得走”的東西,通過高速公路的入口����,走上高速公路,享受學(xué)習(xí)的幸福���。
三����、讓學(xué)成為教學(xué)的核心:課堂教學(xué)必須有重大變革
“帶得走”的東西與高速公路入口���,為著學(xué)生的學(xué)自然地鏈接在一起�。但是,“帶得走”的東西不會自然產(chǎn)生��,當(dāng)下的課堂教學(xué)也產(chǎn)生不了�����。為此����,課堂教學(xué)應(yīng)當(dāng)緊緊圍繞教學(xué)的核心問題��,即圍繞學(xué)生主動學(xué)習(xí)�、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,進(jìn)行一些重大的變革�����。
一是課堂教學(xué)中的師生關(guān)系要發(fā)生重大變革
師生關(guān)系是教育大廈的基石�,不僅是傳統(tǒng)教育的,也應(yīng)是現(xiàn)代教育的����。不過,值得注意的是���,在傳統(tǒng)教育中��,“師生關(guān)系變成了一種統(tǒng)治者和被統(tǒng)治者的關(guān)系”�����,“樹立了具有權(quán)威性的師生關(guān)系典型��,而這種典型仍在全世界大多數(shù)學(xué)校里流行著”���。這種師生關(guān)系的實質(zhì)��,就是教師變成了傳教士�����,而“傳教士曾被當(dāng)作一切知識的托管人與保護(hù)人�����,教育幾乎全在他們的控制之下”����。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��,一針見血地指出,這種師生關(guān)系是一種“陳腐的人際關(guān)系”�。而隨之產(chǎn)生的紀(jì)律是“嚴(yán)格的、權(quán)威性的�、學(xué)院式的”,這種紀(jì)律當(dāng)然也是“陳腐的”��。正是陳腐的權(quán)威性的紀(jì)律���,決定著知識必須由教師傳給學(xué)生�,學(xué)生只能跟著教師亦步亦趨����,教學(xué)過程只能是教的過程����,學(xué)成了教的隨從與附庸。我們應(yīng)當(dāng)勇敢地抵抗這種不民主關(guān)系�,明確教師的身份和職責(zé)。因此����,把教師稱為‘師長'(不管我們給這個名詞一個什么意義),這是越來越濫用的名詞�。教師的職現(xiàn)責(zé)現(xiàn)在已越來越少地傳遞知識,而越來越多地激勵思考……他將越來越成為一位顧問,一位交換意見的參與者��,一位幫助發(fā)現(xiàn)矛盾論點而不是拿出現(xiàn)成真理的人�。我想說的是,教師應(yīng)當(dāng)是幫助學(xué)生���、和學(xué)生一起找到高速公路入口的人�,是激勵和鼓舞學(xué)生主動學(xué)習(xí)的人�����,是知道和幫助學(xué)生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的人�。
師生關(guān)系的民主、和諧���、合作����,不是虛無的���,有時很具體��,不過�����,我以為更為重要的是構(gòu)建課堂教學(xué)文化�,創(chuàng)造課堂中學(xué)生學(xué)習(xí)的環(huán)境和氛圍。首先�,每一個課堂都應(yīng)是一個有著自己價值的團(tuán)體。這個團(tuán)體的紀(jì)律�����、規(guī)則不是教師規(guī)定的�,而是在教師指導(dǎo)下���,學(xué)生們根據(jù)學(xué)習(xí)的需要自己制定的�,紀(jì)律����、規(guī)則不只是規(guī)范學(xué)生��,更不是束縛學(xué)生���,而是為了學(xué)生主動地�、積極也����、創(chuàng)造性地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。這就是共同的課堂教學(xué)價值����。有這樣的價直引領(lǐng)�,學(xué)生可以質(zhì)疑、可以批評�����,甚至可以隨時打斷教師的教授�����。其次�����,創(chuàng)造一個激發(fā)開放式思考與討論的課堂氛圍��。只有當(dāng)學(xué)生不得不自己分析問題時,才會真正進(jìn)入創(chuàng)造性的狀態(tài)���。教師的任務(wù)在于“集中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從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創(chuàng)造性的活動:互相影響、討論����、激勵、了解��、鼓舞”���。在這樣的氛圍中��,學(xué)生才可能主動積極地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。再次,在研究基礎(chǔ)上進(jìn)行教學(xué)����。建立在研究基礎(chǔ)上的教學(xué)是最好的教學(xué)��,這種研究����,不僅是教師課前的研究����,更為重要的是課堂教學(xué)中引導(dǎo)學(xué)生進(jìn)行研究���。也許研究性學(xué)習(xí)目前還不是學(xué)生課堂中主要的學(xué)習(xí)方式,但完全應(yīng)當(dāng)是課堂教學(xué)的主導(dǎo)思想�。
二是課堂教學(xué)結(jié)構(gòu)應(yīng)當(dāng)發(fā)生重大變革
課堂教學(xué)要有更深刻的變革����,就當(dāng)前而言���,教學(xué)結(jié)構(gòu)的變革比教學(xué)方法的變革更為重要��,更為緊迫���。教學(xué)結(jié)構(gòu)變革����,首先是教育理念的變革�,它從根本上落實和體現(xiàn)課程改革新理念�����,并為目標(biāo)的實現(xiàn)提供保障����;教學(xué)結(jié)構(gòu)的變革是全方位的變革�����,不僅涉及教學(xué)內(nèi)容的布局,也不僅涉及教學(xué)時間的分割���,更重要的是教學(xué)重心和教學(xué)重點的設(shè)計與安排,而教學(xué)方法滲透其中��;教學(xué)結(jié)構(gòu)變革實質(zhì)上是教學(xué)框架的重新設(shè)計��,是教學(xué)模式形成的雛型�����。
顯然�����,教學(xué)結(jié)構(gòu)變革的指導(dǎo)思想和基本原則應(yīng)當(dāng)是凸顯學(xué)生主動學(xué)習(xí)這一核心���。觀察一下江蘇泰興市洋思中學(xué)�����、江蘇溧水東廬中學(xué)、山東聊城杜郎口中學(xué),無論是“先學(xué)后教”��,還是以講學(xué)稿為載體“教學(xué)合一”���,抑或是“人人參與�����,個個展示��,嘗試成功��,體驗快樂��,激活思維����,釋放潛能�����,自主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�,個性發(fā)展”,都是在教學(xué)結(jié)構(gòu)上作了大膽的變革��,即以主動學(xué)習(xí)��、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為核心來設(shè)計���,進(jìn)行布局和安排,展開教學(xué)過程�。
教學(xué)結(jié)構(gòu)的變革是一項艱難而復(fù)雜的工作,必須依賴教師的“教育自覺”和駕馭課堂教學(xué)的能力��。這一過程是漫長的���,不妨從以上幾所學(xué)校的改革中汲取一 些做法:一是具有剛性的原則:不學(xué)不教���,先學(xué)后教�,以教導(dǎo)學(xué),以學(xué)促教�����;二是在時間上作些硬性規(guī)定�����。如洋思中學(xué)規(guī)定���,教師一般講課都在10分鐘左右���,最少的甚至只有4-5分鐘�����,學(xué)生自學(xué)學(xué)習(xí)的實間達(dá)到了35-40分鐘之多���。如杜郎口中學(xué)確立“10+35”的課堂教學(xué)模式����,學(xué)生自主學(xué)習(xí)占35分鐘��。這樣的硬性規(guī)定,似乎缺乏科學(xué)性���,未免刻板、僵化����,但仔細(xì)想想���,是很有道理的���,堅持下去,教學(xué)方法的改進(jìn)�����、教學(xué)水平的提高���,必定把教師推向引導(dǎo)者的地位,而把學(xué)生推向主動學(xué)習(xí)�、自主學(xué)習(xí)的地位,漸漸形成習(xí)慣�,最終將形成以學(xué)生學(xué)習(xí)為核心的教學(xué)模式。
當(dāng)然�����,在師生關(guān)系����、課堂教學(xué)結(jié)構(gòu)進(jìn)行重大變革的同時,教學(xué)方式也應(yīng)發(fā)生變革��,以著力指導(dǎo)學(xué)生自主學(xué)習(xí)�。對此,已有很多論述����,本文不再贅述。闡述到這兒���,我們似乎得出一個基本結(jié)論:教學(xué)的核心是使學(xué)生主動學(xué)習(xí)、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;學(xué)生的主動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、學(xué)會學(xué)習(xí)正是那個高速公路的入口處��。